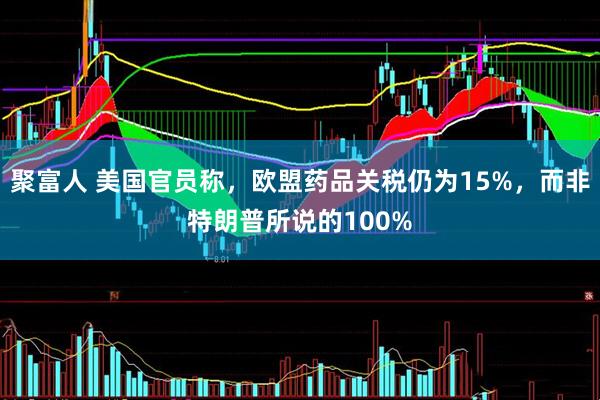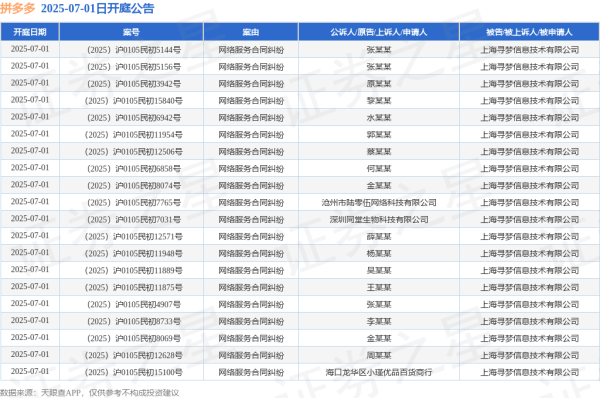“脏唐臭汉”是明清以来流传于民间的戏谑说法贝格富配资,主要针对汉唐两代皇室在伦理道德上的争议行为。这一评价虽带夸张色彩,却折射出汉唐宫廷生活的某些真实侧面,需从历史背景、权力逻辑与文化批判三个维度解析:
一、“臭汉”:汉代宫廷的伦理困境
外戚乱政的腥膻味
吕后毒杀赵王如意、将戚夫人制成“人彘”,开启外干政先河。
霍光家族“二十年间骨肉相残”(《汉书》),汉哀帝与男宠董贤“断袖”典故,使皇权蒙上私情阴影。
近亲婚配的生理尴尬
汉惠帝被迫娶亲外甥女张嫣(吕后操纵),《汉宫春色》载张嫣至死仍是处女。
汉武帝“金屋藏娇”娶表姐陈阿娇,后因无子废黜引发巫蛊之祸,牵连数万人。
荒淫君主的象征符号
汉成帝与赵飞燕姐妹“温柔乡”典故,史载“昼御数女”,最终暴毙在赵合德床榻。
民间将汉代宫闱秘事编入《飞燕外传》等小说,强化“臭”的感官联想。
二、“脏唐”:唐代宫廷的欲望迷宫
血亲伦理的突破贝格富配资
唐太宗纳弟媳杨氏(齐王妃),高宗李治娶父亲才人武则天,玄宗夺儿媳杨玉环。
白居易《长恨歌》“从此君王不早朝”成讽刺标签,朱熹斥为“人伦之大变”。
女性掌权的道德围剿
武则天养男宠张昌宗兄弟,上官婉儿“淫乱宫闱”的野史记载。
太平公主献男宠给武则天,韦后与武三思私通,被道学家视为“牝鸡司晨”的恶果。
开放风气的妖魔化
唐代公主再嫁者达23人(如高阳公主私通辩机和尚),与理学“从一而终”冲突。
宫廷盛行“春宫秘戏图”(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实物),成为宋明卫道士攻击靶标。
三、话语生成:明清道德审判的产物
理学对汉唐的“降维打击”
程朱理学将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神圣化,以宋代贞节观(如《程氏遗书》“饿死事小”)审判前朝。
唐代敦煌文书显示贝格富配资,妇女离婚书写“愿相离后各生欢喜”,在明清已成不可想象之举。
小说戏剧的推波助澜
《隋唐演义》渲染李世民杀兄逼父,《如意君传》虚构武则天淫行,使历史被情色化叙事覆盖。
京剧《贵妃醉酒》本写杨玉环苦闷,却被解读为“放荡醉态”。
权力更替的隐喻需要
明朝贬低元朝“胡俗乱华”后,需塑造更早的反面典型以证正统。
清朝借批判汉唐“失德”,强调自身“整顿风化”的合法性(如乾隆禁毁《汉宫秘史》)。
四、历史再思考:突破污名化叙事
时代语境的错位批判
汉代近亲婚延续周代“媵妾制”(如鲁昭公娶吴孟子),当时视为政治联姻常态。
唐代收继婚含鲜卑遗风,武则天嫁父子在突厥习俗中并不异常。
权力结构的必然产物
汉唐宫廷乱象本质是绝对权力腐蚀伦理:后宫制度使人伦异化,外戚宦官是皇权延伸的毒瘤。
对比欧洲王室: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娶妓女狄奥多拉,法王亨利二世情妇成群。
文明贡献的遮蔽效应
汉代开拓西域、唐代包容胡风,推动文明交流的功绩被“脏臭”标签掩盖。
班昭《女诫》与宋若莘《女论语》证明汉唐本身存在道德自省,非全然放纵。
结语:污名背后的文化密码
“脏唐臭汉”实则是宋明理学对汉唐气魄的恐惧投射——当汉家“犯强汉者虽远必诛”的雄浑,唐室“胡姬压酒劝客尝”的开放,遭遇宋后内敛保守的伦理体系时,那些蓬勃的生命力便被污名为“脏臭”。
理解此说,需穿透道德批判的表象,看到三种文明的碰撞:
汉代是农耕文明建立伦理秩序的探索之痛,
唐代是胡汉融合中欲望与权力的混沌实验,
明清则是礼教对野性基因的焦虑绞杀。
若抛开猎奇视角,汉唐的“脏臭”恰是华夏文明强盛期未被礼教阉割的生命力证明,正如尼采所言:“道德是弱者用来束缚强者的工具。”
通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